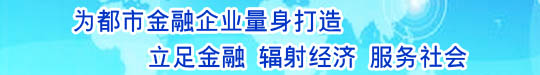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丝绸之路托起唐代边塞诗的繁盛
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息息相通,无数唐代文人或游边、或入幕、或奉使,行进在古老的丝绸之路,写下了壮丽多姿的边塞诗,构成了盛唐最华丽的乐章之一。
初唐杨炯的名篇《从军行》中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,表达了一代文人的价值选择,“投笔从戎”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签。与中原相比,边塞奇丽而苦寒的自然风光,紧张而动荡的军旅生活,以及多彩多姿的异域风土人情,激发着唐代士人。或许可以说,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。
从长安西去踏上丝绸之路,第一道自然屏障即为陇山。陇山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,隔断了秦陇两地,分开了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,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线,是京畿内地与边关塞外的分界线。岑参作为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,其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写道:“十日过沙碛,终朝风不休。马走碎石中,四蹄皆血流。”诗中所写当是诗人的耳闻,却也透露出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心理感受与无限遐想。高适的陇头诗歌则多写得慷慨激昂,如《独孤判官部送兵》:“出关逢汉壁,登陇望胡天。亦是封侯地,期君早着鞭。”征人登陇而激扬风发的英雄豪情,表露出悲壮的美感。
翻越陇头,经过南北两路皆可到达凉州,凉州自古以来为河陇重镇。盛唐时期尤为繁荣。岑参的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曰:“弯弯月出挂城头,城头月出照凉州。凉州七里十万家,胡人半解弹琵琶。”于凉州歌舞繁华刻画中可见诗人之豪情。
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玉门关,扼守丝绸之路要冲,也是唐代诗人着意刻画的西域门户。自汉代班超上疏曰:“不敢望到酒泉郡,但愿生入玉门关。”“生入玉门”,乃成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头禅。晚唐胡曾《咏史·玉门关》咏叹“西戎不敢过天山,定远功成白马闲。半夜帐中停烛坐,唯思生入玉门关。”戴叔伦反其意而用之:“汉家旌帜满阴山,不遣胡儿匹马还。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“阳关”作为一个意象,也是进入绝域的门户,又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,唐诗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诗中写到阳关的不少,如王维名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、耿湋《陇西行》等。在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人中,岑参也最有代表性。
西州境内的交河城地势险要,安西大都护府最初即选择设在这里。这里是丝绸之路中的交通要道,在不少诗人笔下,交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,交河冬寒、征戍之苦成为诗人常写的意象。如虞世南《出塞》:“凛凛边风急,萧萧征马烦。雪暗天山道,冰塞交河源。”骆宾王有《从军中行路难》诗云:“阴山苦雾埋高垒,交河孤月照连营。”孟郊《折杨柳》写道:“花惊燕地云,叶映楚池波。谁堪别离此,征戍在交河。”陈陶《水调词十首》更从征夫思妇着笔:“长夜孤眠倦锦衾,秦楼霜月苦边心。征衣一倍装绵厚,犹虑交河雪冻深。”在这些诗里,交河已是象征边塞的文化符号。
至于轮台、北庭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于阗等地,唐代边塞诗中亦多有描写,唐代西部的边塞诗歌,通过形象的诗歌语言勾画出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,可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感性资料。丝路景观也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,成为诗人抒情的触媒。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。
其一,丝路文化影响唐代边塞诗的精神风貌。丝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唐代中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。
其二,丝绸之路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。古人云文学得江山之助,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也得到丝路之助。一方面,丝路上的自然景观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全面翔实的刻画,大量的边塞诗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丝路风光的全景图。另一方面,这种文化景观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写实,而上升为蕴含着丰富历史与人文内涵的文化符号,前文分析的陇头、凉州、阳关、玉门关莫不如此,不仅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,也深深地影响了边塞诗的风格与意境。
其三,丝路景观作为触媒影响边塞诗的情感抒发。在唐人心目中,边塞是地理分界线,也是文化、风俗与心理的分界线,以及家园与绝域的分界线。因此,除了客观的写实,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边塞诗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边塞成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号,丝路风景也成为激发诗思的触媒,古典诗歌常写的思亲念友、聚散匆匆,报国心切、岁月空老,人生苦短、功业难建,征戍无期、归家无计等,这些平常之情均在边塞背景下得到激发和强化,从而汇成丰富多彩的多元特色。因而,唐代边塞诗中蕴含的情感如同西域的美酒,显得更为浓烈,值得细细品味。林越
初唐杨炯的名篇《从军行》中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,表达了一代文人的价值选择,“投笔从戎”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签。与中原相比,边塞奇丽而苦寒的自然风光,紧张而动荡的军旅生活,以及多彩多姿的异域风土人情,激发着唐代士人。或许可以说,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。
从长安西去踏上丝绸之路,第一道自然屏障即为陇山。陇山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,隔断了秦陇两地,分开了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,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线,是京畿内地与边关塞外的分界线。岑参作为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,其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写道:“十日过沙碛,终朝风不休。马走碎石中,四蹄皆血流。”诗中所写当是诗人的耳闻,却也透露出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心理感受与无限遐想。高适的陇头诗歌则多写得慷慨激昂,如《独孤判官部送兵》:“出关逢汉壁,登陇望胡天。亦是封侯地,期君早着鞭。”征人登陇而激扬风发的英雄豪情,表露出悲壮的美感。
翻越陇头,经过南北两路皆可到达凉州,凉州自古以来为河陇重镇。盛唐时期尤为繁荣。岑参的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曰:“弯弯月出挂城头,城头月出照凉州。凉州七里十万家,胡人半解弹琵琶。”于凉州歌舞繁华刻画中可见诗人之豪情。
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玉门关,扼守丝绸之路要冲,也是唐代诗人着意刻画的西域门户。自汉代班超上疏曰:“不敢望到酒泉郡,但愿生入玉门关。”“生入玉门”,乃成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头禅。晚唐胡曾《咏史·玉门关》咏叹“西戎不敢过天山,定远功成白马闲。半夜帐中停烛坐,唯思生入玉门关。”戴叔伦反其意而用之:“汉家旌帜满阴山,不遣胡儿匹马还。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“阳关”作为一个意象,也是进入绝域的门户,又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,唐诗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诗中写到阳关的不少,如王维名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、耿湋《陇西行》等。在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人中,岑参也最有代表性。
西州境内的交河城地势险要,安西大都护府最初即选择设在这里。这里是丝绸之路中的交通要道,在不少诗人笔下,交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,交河冬寒、征戍之苦成为诗人常写的意象。如虞世南《出塞》:“凛凛边风急,萧萧征马烦。雪暗天山道,冰塞交河源。”骆宾王有《从军中行路难》诗云:“阴山苦雾埋高垒,交河孤月照连营。”孟郊《折杨柳》写道:“花惊燕地云,叶映楚池波。谁堪别离此,征戍在交河。”陈陶《水调词十首》更从征夫思妇着笔:“长夜孤眠倦锦衾,秦楼霜月苦边心。征衣一倍装绵厚,犹虑交河雪冻深。”在这些诗里,交河已是象征边塞的文化符号。
至于轮台、北庭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于阗等地,唐代边塞诗中亦多有描写,唐代西部的边塞诗歌,通过形象的诗歌语言勾画出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,可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感性资料。丝路景观也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,成为诗人抒情的触媒。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。
其一,丝路文化影响唐代边塞诗的精神风貌。丝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唐代中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。
其二,丝绸之路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。古人云文学得江山之助,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也得到丝路之助。一方面,丝路上的自然景观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全面翔实的刻画,大量的边塞诗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丝路风光的全景图。另一方面,这种文化景观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写实,而上升为蕴含着丰富历史与人文内涵的文化符号,前文分析的陇头、凉州、阳关、玉门关莫不如此,不仅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,也深深地影响了边塞诗的风格与意境。
其三,丝路景观作为触媒影响边塞诗的情感抒发。在唐人心目中,边塞是地理分界线,也是文化、风俗与心理的分界线,以及家园与绝域的分界线。因此,除了客观的写实,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边塞诗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边塞成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号,丝路风景也成为激发诗思的触媒,古典诗歌常写的思亲念友、聚散匆匆,报国心切、岁月空老,人生苦短、功业难建,征戍无期、归家无计等,这些平常之情均在边塞背景下得到激发和强化,从而汇成丰富多彩的多元特色。因而,唐代边塞诗中蕴含的情感如同西域的美酒,显得更为浓烈,值得细细品味。林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