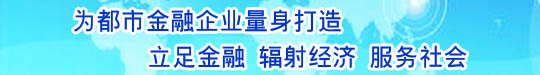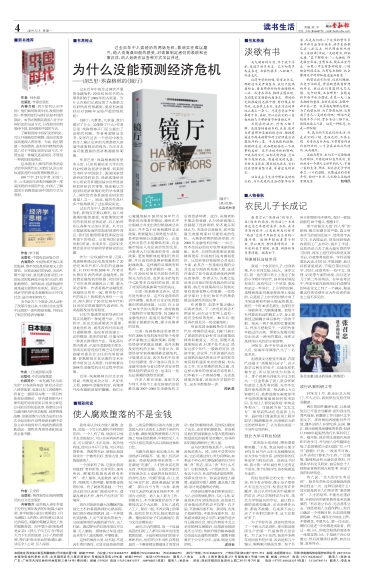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农民儿子长成记
张召忠以“悄悄话”的形式,在《进击的局座:悄悄话》一书里讲述自己年轻时求学、当兵、成为学者的经历,以及被网友们称作“局座”受到千万粉丝关注后的心路历程。鼓励年轻读者勇于创新、学以致用、理性看待现实。本书还科普了国防、兵器、网络战等军事问题。摘录如下。
导弹部队当技术兵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出身贫寒,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。18岁之前,我一直在那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,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,没有吃过一个苹果,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。上小学的时候,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,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。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,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,大家睡通铺。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,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。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,外加几把地瓜干,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。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的霉丝,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。
1970年,我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,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。
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,在部队还属于“高级知识分子”,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、无线电和机械专业,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。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,一旦业务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,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。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,我都是藏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,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“单纯业务观点”。可能因为我“又红又专”,领导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。最初是打算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,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,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。
到北大学习阿拉伯语
“革命战士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于是,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,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。直到这个时候,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,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。
阿拉伯语和它的文化一样古老,样子有点特别,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,发音还有许多颤音,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,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,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。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,无论我费多大劲,都发不准确。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,这下总算好多了。
为了学好外语,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,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。为了这个小东西,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炒菜,天天是抓几个馒头,喝两碗大锅汤完事。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,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,整整2斤。
那个时候北大受“四人帮”的影响,极左思潮非常严重,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,经常是半天学习,半天搞运动,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,搞半工半读。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,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,行政事务也很多。学外语需要天天读,时时记,不能间断,我只好抓紧星期天、节假日等时间自学,同时,还喜欢听一些中文、地理、历史等方面的讲座,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。在毕业考试中,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,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改行从事科研工作
1978年1月,我走出北大校门,不久之后,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。
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,让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当翻译,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,而翻译工作只能从文字到文字。那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,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,出国、赚汇、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,但我从1980年起毅然改行从事科研工作。刚开始,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,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《追踪“红十月号”潜艇》,从此,一发而不可收。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,广泛搜集、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,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,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,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。
有人说,“北大的学生有后劲”。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这种后劲是什么?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“素质教育”。人才的培养,不能光注重分数,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。“有志者立长志,无志者常立志。”我经常把人生看作爬山,你自己确定一个终极目标,比如是珠穆朗玛峰。然后,竭尽全力地往上爬,不要着急,不要灰心,要一往无前,哪怕只前进一步你都是成功者。爬过一座山头,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头,于是就下决心征服它,然后再继续往前爬,如此往复,直至终点。
导弹部队当技术兵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出身贫寒,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。18岁之前,我一直在那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,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,没有吃过一个苹果,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。上小学的时候,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,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。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,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,大家睡通铺。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,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。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,外加几把地瓜干,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。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的霉丝,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。
1970年,我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,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。
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,在部队还属于“高级知识分子”,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、无线电和机械专业,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。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,一旦业务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,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。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,我都是藏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,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“单纯业务观点”。可能因为我“又红又专”,领导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。最初是打算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,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,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。
到北大学习阿拉伯语
“革命战士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于是,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,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。直到这个时候,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,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。
阿拉伯语和它的文化一样古老,样子有点特别,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,发音还有许多颤音,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,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,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。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,无论我费多大劲,都发不准确。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,这下总算好多了。
为了学好外语,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,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。为了这个小东西,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炒菜,天天是抓几个馒头,喝两碗大锅汤完事。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,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,整整2斤。
那个时候北大受“四人帮”的影响,极左思潮非常严重,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,经常是半天学习,半天搞运动,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,搞半工半读。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,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,行政事务也很多。学外语需要天天读,时时记,不能间断,我只好抓紧星期天、节假日等时间自学,同时,还喜欢听一些中文、地理、历史等方面的讲座,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。在毕业考试中,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,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改行从事科研工作
1978年1月,我走出北大校门,不久之后,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。
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,让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当翻译,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,而翻译工作只能从文字到文字。那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,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,出国、赚汇、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,但我从1980年起毅然改行从事科研工作。刚开始,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,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《追踪“红十月号”潜艇》,从此,一发而不可收。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,广泛搜集、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,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,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,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。
有人说,“北大的学生有后劲”。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这种后劲是什么?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“素质教育”。人才的培养,不能光注重分数,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。“有志者立长志,无志者常立志。”我经常把人生看作爬山,你自己确定一个终极目标,比如是珠穆朗玛峰。然后,竭尽全力地往上爬,不要着急,不要灰心,要一往无前,哪怕只前进一步你都是成功者。爬过一座山头,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头,于是就下决心征服它,然后再继续往前爬,如此往复,直至终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