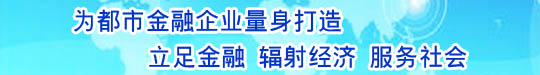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粟特商人推动了丝路贸易
一些人常常问:丝绸之路上进行的大多是小额贸易?谁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?丝绸之路上唐朝官府如何管理丝路贸易?
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认为,不能仅仅依据出土的商业契约来推断丝路上的贸易规模,商业契约毕竟只是贸易最终完成的末端文献。吐鲁番出土的称价文书表明,当时的高昌国内已有较大规模的丝织品市场,而贩卖丝绸的商人是粟特人,这一群体人数众多,他们有的在中国定居,并诞生一批名人扬名后世,比如安禄山。
1907年,斯坦因在长城烽燧下面发掘到一个麻布邮包,包里装着八九封信。信是从敦煌、酒泉、武威寄出的。保存得最好的是二号信札,信上说匈奴人打进洛阳,皇帝都跑了,我们商人饥寒交迫快死了。写这信的人是以武威为大本营的粟特商队首领。
粟特人做生意往往会结成商队,到了一个地方停留,形成聚落,商队首领叫“萨保”。粟特商队留下一拨人,一拨人又往前走,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贸易网络。写信的这个武威粟特商人讲到,他派了一些商人到邺城去做生意,又派了一些人到洛阳、兰州、酒泉、敦煌。我们曾经认为,粟特商人一般是自西向东做生意,文书告诉我们,粟特商人是以一个地方作大本营,向四面八方分散着贸易。
商人倒来的东西主要是金银黄铜等贵金属,还有香料、药材,倒出去的最主要的就是丝绸。
此外,粟特商人还是人口贩子。商品单子里有很多小姑娘和小男孩。为什么长安城里有那么多胡姬?这都是他们倒来的,所以唐朝市场里有个“口马市”,口是人口,马是牲口,一起卖。
有份文书是天宝二年的交河郡(今吐鲁番)市估案。唐朝市场管理体制是,商品上市前要估三个价,上中下三个价钱,估好后写成文书报给官府,官府说可以,你就买卖。再把价目放到市场里。其中有帛练行、綵帛行,专门卖丝制品。当然也有口马行、蔬菜行等等。
这些东西主要是卖给粟特商人,所以,你不能说吐鲁番文书说没有商人做买卖的记录,就说此地不存在商业交易。吐鲁番的普通老百姓能经常逛这么高档的丝织品商场吗?还不是商人来买。
有个文献是“称价钱”文书,即高昌王国向市场上买卖双方征的商业税。上面有“买金九两半,买银五斤,买药一百四十斤”,“买丝五十斤”等内容。我们注意到,买卖双方几乎都有康、安、曹、何等明显的粟特姓氏,也就是说运商品来的是粟特商人,当地收商品的也是粟特商人。商人们收了之后再倒卖,倒一笔赚一笔,各赚各的,一个商品从吐鲁番运到长安,转了好几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。
第二,我们注意到,这些做买卖的有部分是批发商,做的是大买卖。我们不能按照后来成交的契约,来判定买卖的规模。那些文书是商品购进之后,分散到市场上卖给个人,才形成的。这是批发之后,下一步的事。这个商队的规模,怎么运营,我们还得用文书做合理的推论。
“称价钱”文书跟粟特文古信札记录正好相符,文书上记着运来的是奢侈品、贵重金属,拿走的是丝绸。我们看到一个萨保,不能理解为个体,一个萨保必定是一个商队,这个商队没有上百人,根本不敢翻塔什库尔干(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,位于喀什地区)的那条路,如果只是几个商人,早就被强盗干掉了。
粟特商人是国际商贩。北齐跟吐谷浑做生意,是让粟特商人做的。结果粟特人过凉州武威的时候,被另一个在北周当官的粟特首领给侦查到了,半路抢劫,获“商胡二百多人,杂采上万匹”。这能是小的商队吗?这还只是从山东跑到青海的人。胡俑
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认为,不能仅仅依据出土的商业契约来推断丝路上的贸易规模,商业契约毕竟只是贸易最终完成的末端文献。吐鲁番出土的称价文书表明,当时的高昌国内已有较大规模的丝织品市场,而贩卖丝绸的商人是粟特人,这一群体人数众多,他们有的在中国定居,并诞生一批名人扬名后世,比如安禄山。
1907年,斯坦因在长城烽燧下面发掘到一个麻布邮包,包里装着八九封信。信是从敦煌、酒泉、武威寄出的。保存得最好的是二号信札,信上说匈奴人打进洛阳,皇帝都跑了,我们商人饥寒交迫快死了。写这信的人是以武威为大本营的粟特商队首领。
粟特人做生意往往会结成商队,到了一个地方停留,形成聚落,商队首领叫“萨保”。粟特商队留下一拨人,一拨人又往前走,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贸易网络。写信的这个武威粟特商人讲到,他派了一些商人到邺城去做生意,又派了一些人到洛阳、兰州、酒泉、敦煌。我们曾经认为,粟特商人一般是自西向东做生意,文书告诉我们,粟特商人是以一个地方作大本营,向四面八方分散着贸易。
商人倒来的东西主要是金银黄铜等贵金属,还有香料、药材,倒出去的最主要的就是丝绸。
此外,粟特商人还是人口贩子。商品单子里有很多小姑娘和小男孩。为什么长安城里有那么多胡姬?这都是他们倒来的,所以唐朝市场里有个“口马市”,口是人口,马是牲口,一起卖。
有份文书是天宝二年的交河郡(今吐鲁番)市估案。唐朝市场管理体制是,商品上市前要估三个价,上中下三个价钱,估好后写成文书报给官府,官府说可以,你就买卖。再把价目放到市场里。其中有帛练行、綵帛行,专门卖丝制品。当然也有口马行、蔬菜行等等。
这些东西主要是卖给粟特商人,所以,你不能说吐鲁番文书说没有商人做买卖的记录,就说此地不存在商业交易。吐鲁番的普通老百姓能经常逛这么高档的丝织品商场吗?还不是商人来买。
有个文献是“称价钱”文书,即高昌王国向市场上买卖双方征的商业税。上面有“买金九两半,买银五斤,买药一百四十斤”,“买丝五十斤”等内容。我们注意到,买卖双方几乎都有康、安、曹、何等明显的粟特姓氏,也就是说运商品来的是粟特商人,当地收商品的也是粟特商人。商人们收了之后再倒卖,倒一笔赚一笔,各赚各的,一个商品从吐鲁番运到长安,转了好几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。
第二,我们注意到,这些做买卖的有部分是批发商,做的是大买卖。我们不能按照后来成交的契约,来判定买卖的规模。那些文书是商品购进之后,分散到市场上卖给个人,才形成的。这是批发之后,下一步的事。这个商队的规模,怎么运营,我们还得用文书做合理的推论。
“称价钱”文书跟粟特文古信札记录正好相符,文书上记着运来的是奢侈品、贵重金属,拿走的是丝绸。我们看到一个萨保,不能理解为个体,一个萨保必定是一个商队,这个商队没有上百人,根本不敢翻塔什库尔干(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,位于喀什地区)的那条路,如果只是几个商人,早就被强盗干掉了。
粟特商人是国际商贩。北齐跟吐谷浑做生意,是让粟特商人做的。结果粟特人过凉州武威的时候,被另一个在北周当官的粟特首领给侦查到了,半路抢劫,获“商胡二百多人,杂采上万匹”。这能是小的商队吗?这还只是从山东跑到青海的人。胡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