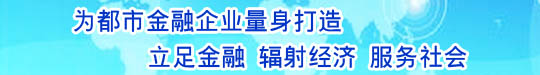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记儿时看的露天电影
英国诗人库柏说过,城市是人类造的,而乡村,则是上帝的手笔。是的,一切的简朴之物,包括人和事,都是自然的初心。
我生来第一次看的电影,是我的母亲抱着我看的,但是电影的名字,已经失记了。
我那时不知几岁,只记得自己是睡在一个木摇桶里,那摇桶我们称作“科桶”,我的姐姐,则睡在另一个大些的摇床里,她比我大两岁。这个电影,是在我们村东头的老柿树下放的,离我家屋子不远。我是第一个要求去看的,但因为我小,怕吓着了我,我的祖母没同意,并且我母亲也只能抱一个孩子,所以就是我姐姐去了。我的扫兴可想而知,但出人意外的,电影放到中间,母亲抱着姐姐回来了,姐姐还在哭,那是被电影吓的。电影是一部战争片。小的时候,我对姐姐总有些轻视,嫌她太弱了,我不但比她大胆得多,身体也要结实,见她回来了,又哭着,我心里很高兴,就再次要求去看,说我是不怕的,最喜欢看打仗,祖母终于同意了。母亲又抱着我去,经过石头地,夜很黑,我听到那个放电影的发电机的声音,在隆隆作响,到了放映之处,也就是数百步,不知为何,母亲不肯再进正面看电影的人群中,而只是抱着我站在老柿树的背面看那个电影的幕布。所以,这个平生第一次看的电影,我只看了后半场,并且是从反面看的。
另一部电影,也是只记得一个镜头,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则是我五岁时看的。我的伯父有一个女婿,姓方,其家在浮山不远处,有一阵子,我总是跟着祖母去他家,一住好几天。有时候,甚至我的祖母回去了,我还留在他家。看电影的那晚上,这个姐夫是把我架在他肩上,即所谓的“架马肩”,去到五六里地外的一个村子,看那部电影的。“架马肩”时,小孩两腿向前分开,坐于大人肩膀,小孩可抱大人之头,大人则捉小孩之腿,以免倾跌。看电影时,从头至尾我都是这样坐法的,姐夫那时正当年轻,大概并不费力。那天晚上看的电影,也是打仗的片子,我所记得的,是有一个小八路,从敌人的马房解了一匹马,骑上就跑,后面的一伙敌人紧追不舍,使我着急的是,不知为什么,那个小八路骑在马上,固然那匹马跑得似乎非常之快,但看起来,却又是不停地在原地踏步,压根儿不移动,而同样奇怪的,是后面追他的人,也一直在后面追他不上。这就使我一面急,一面又大惑不解,那个心理和电影的画面,在记忆中极其深刻,现在回想起来,也清楚不过。但整部的电影中,记得起的也只有这个镜头而已。
我小时觉得最好看的电影之一的,是万古蟾导演的《渔童》。我本来像许多人一样,以为那个电影叫《聚宝盆》,因为电影里的那个小孩,就是画在盆里的,但是搜检了网上,才知不是的。电影里的小孩,特别的神气,在同为小孩子的我的眼里,那当然无比带劲了。电影拍于1959年,但我看的时候,已是七十年代中期,电影中的故事,那个盆中小孩的动作及样子,我大多还记得,就是放电影的那个村庄,那个晚上的夜色,看了电影后大家在回家路上的谈说,也是犹存于记忆,只是觉得遥远不可及罢了。
更晚一些而又更觉好看的,无疑是《大闹天宫》。《大闹天宫》是1964年拍的,是万古蟾的哥哥即被称为“大万老”的万籁鸣所执导,它的上映时间,第二次在1978年,我看《大闹天宫》,也就是这一年,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。得知放这电影的那个下午,我在家又叫又跳的,按捺不住。大闹天宫,孙悟空,一听这几个字,就让人兴奋不已。在那个时代,是没有小孩子不喜欢孙悟空的,也没有小孩子不对大闹天宫那一个故事,充满神往之情。只是说来好笑,电影中的情节,于我印象最深、看时也最为瞩目的,并不是孙悟空的变化神通,也不是他与各路大神的斗战,而是他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桃子,并且可以将身子变小,躺在桃子上,尽情饱啖,而自在之极,那实在是最让我羡慕的事。也许,我小的时候是以吃为第一快事的,所以在看电影时,也就不由自主专注于此了。一切印象深刻之处,就是注意力专注的所在,注意力专注之处,也就是一个人的平生快乐之事。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假借的。
但那时更多的电影,则是我们国内的战争片,如《蒙根花》《吉鸿昌》《从奴隶到将军》《济南战役》《智取华山》《曙光》等。看过的外国战争片,可能只有一部南斯拉夫的《桥》。《桥》是1969年的电影,我看的时候,可能是与《曙光》同时的,从打仗的角度说,《桥》是更好看的电影,因为特别的激烈,尤其那一段在河中边退却边与敌人互相对射,持续时间之长,是那时所不曾见过的。
《曙光》中所记得的一个细节,是贺龙在前线指挥时,有一颗子弹飞来,射入他的军帽了,他摘下帽子,只见帽上打了一个洞,那真是危险,他却只用手掸了下,笑骂了一句,那种满不在乎等闲而视之的神情,使得我对他非常之佩服。看了那个电影,再加上我更小的时候,在一本伯父给的《革命故事会》中所读到的“两把菜刀闹革命”的贺龙的故事,我便说要做贺龙。有一次,我生病了,母亲带我去看医生,那医生姓徐,是一位熟人,母亲和他说话时,带及此事,医生说:中国只有一个贺龙,你怎么做他?我不能接他的话锋,大是羞惭,心里怪母亲,为什么连这个也说。那时我已八九岁了。《从奴隶到将军》是在我们小学校旁边放的,名字就吸引人,更不必提它的故事了,其实在我小时,只要是打仗的电影,我都认为是好看的,我的伯父跟我意见完全一致,并且凡是我认为好看的,他也就认为好。而不少电影,也正是伯父带着我去看的,像上面提的这些,都是。
那时最不喜欢的电影,是著名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不用说,这是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,其片长达三个半小时,分为上下集,但我只看了上集,那时也只放了上集,是东村的人放的。电影里的镜头,记得起的很多,如张忠良演说时在黑板徒手画地图,忠良的老父被日本兵在树上吊死,白杨演的素芬给小孩补裤子屁股那儿的破洞,还有那个王丽珍给她干爹打电话,嗲声嗲气。上集的后面,是屋外下着大雨,素芬和她婆婆在床上,屋里到处在漏水。这是人间的悲苦,看了让人抑郁难过。二十年后,我在电视上又看了费穆导的《小城之春》,那也是解放前的老电影,拍于这部的后一年,也就是1948年。当时是从中间看的,一直就看到了结束,毫不枯燥。有人称《小城之春》为银幕抒情诗,大概不算过分,从艺术上说,它们有可一比,可以双峰并峙。但就是《小城之春》,我也不想再看,因为故事太单调,而气氛又太抑郁了。就像我后来看过的美国米高梅公司的《十二怒汉》,也无疑是一部杰作,其匠心独运之处,令人叹绝,但同样也是看过就不想再看了。有时候,你所喜欢的,不一定就是你认为最好的,而你认为是好的,却又不一定是你喜欢的,人就是这样的矛盾。看电影是如此,读书也是如此,就是穿衣、吃饭及行事,也莫不如此。
那时的电影,是由各村子出钱,请县里的放映人员来放,所有的电影,都是在露天看的,看电影的人,也只要晚上跑路(但对我来说,也有因为夜黑路远而不被允许去看、因而错过的电影,如《黑三角》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《神秘的大佛》《画皮》等),自带椅凳,不必花钱买票。也就是说,那时的所有电影,无不是免费的。小孩子个子小,必须站在凳子上,才能看得到,所以往往要扛长凳。放映的时候,也有挑着甘蔗来卖的,边看电影边吃甘蔗,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我家的家教严,从没有买过甘蔗吃。有小包装的葵花籽卖的,又是晚一些时候的事了,那应该是1983年后才有的,那时已建了电影院,很少再露天放电影,看露天电影的时代从此过去了。
从那以后,我看电影也就少了,我所记得的,在电影院看的电影,有《西安事变》,有《四渡赤水》,还有潘虹主演的《杜十娘》。无论如何,这些电影的味道,在我看来总不及在露天里看的好,看电影前的买票之拥挤、喧嚷、争执,看电影时的屋子之窘狭、气闷,都使人生出不适,减损了电影本身的快乐。而城市的坏处,在电影院看电影时,我也初见了端倪。
英国诗人库柏说过,城市是人类造的,而乡村,则是上帝的手笔。是的,一切的简朴之物,包括人和事,都是自然的初心。
我生来第一次看的电影,是我的母亲抱着我看的,但是电影的名字,已经失记了。
我那时不知几岁,只记得自己是睡在一个木摇桶里,那摇桶我们称作“科桶”,我的姐姐,则睡在另一个大些的摇床里,她比我大两岁。这个电影,是在我们村东头的老柿树下放的,离我家屋子不远。我是第一个要求去看的,但因为我小,怕吓着了我,我的祖母没同意,并且我母亲也只能抱一个孩子,所以就是我姐姐去了。我的扫兴可想而知,但出人意外的,电影放到中间,母亲抱着姐姐回来了,姐姐还在哭,那是被电影吓的。电影是一部战争片。小的时候,我对姐姐总有些轻视,嫌她太弱了,我不但比她大胆得多,身体也要结实,见她回来了,又哭着,我心里很高兴,就再次要求去看,说我是不怕的,最喜欢看打仗,祖母终于同意了。母亲又抱着我去,经过石头地,夜很黑,我听到那个放电影的发电机的声音,在隆隆作响,到了放映之处,也就是数百步,不知为何,母亲不肯再进正面看电影的人群中,而只是抱着我站在老柿树的背面看那个电影的幕布。所以,这个平生第一次看的电影,我只看了后半场,并且是从反面看的。
另一部电影,也是只记得一个镜头,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则是我五岁时看的。我的伯父有一个女婿,姓方,其家在浮山不远处,有一阵子,我总是跟着祖母去他家,一住好几天。有时候,甚至我的祖母回去了,我还留在他家。看电影的那晚上,这个姐夫是把我架在他肩上,即所谓的“架马肩”,去到五六里地外的一个村子,看那部电影的。“架马肩”时,小孩两腿向前分开,坐于大人肩膀,小孩可抱大人之头,大人则捉小孩之腿,以免倾跌。看电影时,从头至尾我都是这样坐法的,姐夫那时正当年轻,大概并不费力。那天晚上看的电影,也是打仗的片子,我所记得的,是有一个小八路,从敌人的马房解了一匹马,骑上就跑,后面的一伙敌人紧追不舍,使我着急的是,不知为什么,那个小八路骑在马上,固然那匹马跑得似乎非常之快,但看起来,却又是不停地在原地踏步,压根儿不移动,而同样奇怪的,是后面追他的人,也一直在后面追他不上。这就使我一面急,一面又大惑不解,那个心理和电影的画面,在记忆中极其深刻,现在回想起来,也清楚不过。但整部的电影中,记得起的也只有这个镜头而已。
我小时觉得最好看的电影之一的,是万古蟾导演的《渔童》。我本来像许多人一样,以为那个电影叫《聚宝盆》,因为电影里的那个小孩,就是画在盆里的,但是搜检了网上,才知不是的。电影里的小孩,特别的神气,在同为小孩子的我的眼里,那当然无比带劲了。电影拍于1959年,但我看的时候,已是七十年代中期,电影中的故事,那个盆中小孩的动作及样子,我大多还记得,就是放电影的那个村庄,那个晚上的夜色,看了电影后大家在回家路上的谈说,也是犹存于记忆,只是觉得遥远不可及罢了。
更晚一些而又更觉好看的,无疑是《大闹天宫》。《大闹天宫》是1964年拍的,是万古蟾的哥哥即被称为“大万老”的万籁鸣所执导,它的上映时间,第二次在1978年,我看《大闹天宫》,也就是这一年,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。得知放这电影的那个下午,我在家又叫又跳的,按捺不住。大闹天宫,孙悟空,一听这几个字,就让人兴奋不已。在那个时代,是没有小孩子不喜欢孙悟空的,也没有小孩子不对大闹天宫那一个故事,充满神往之情。只是说来好笑,电影中的情节,于我印象最深、看时也最为瞩目的,并不是孙悟空的变化神通,也不是他与各路大神的斗战,而是他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桃子,并且可以将身子变小,躺在桃子上,尽情饱啖,而自在之极,那实在是最让我羡慕的事。也许,我小的时候是以吃为第一快事的,所以在看电影时,也就不由自主专注于此了。一切印象深刻之处,就是注意力专注的所在,注意力专注之处,也就是一个人的平生快乐之事。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假借的。
但那时更多的电影,则是我们国内的战争片,如《蒙根花》《吉鸿昌》《从奴隶到将军》《济南战役》《智取华山》《曙光》等。看过的外国战争片,可能只有一部南斯拉夫的《桥》。《桥》是1969年的电影,我看的时候,可能是与《曙光》同时的,从打仗的角度说,《桥》是更好看的电影,因为特别的激烈,尤其那一段在河中边退却边与敌人互相对射,持续时间之长,是那时所不曾见过的。
《曙光》中所记得的一个细节,是贺龙在前线指挥时,有一颗子弹飞来,射入他的军帽了,他摘下帽子,只见帽上打了一个洞,那真是危险,他却只用手掸了下,笑骂了一句,那种满不在乎等闲而视之的神情,使得我对他非常之佩服。看了那个电影,再加上我更小的时候,在一本伯父给的《革命故事会》中所读到的“两把菜刀闹革命”的贺龙的故事,我便说要做贺龙。有一次,我生病了,母亲带我去看医生,那医生姓徐,是一位熟人,母亲和他说话时,带及此事,医生说:中国只有一个贺龙,你怎么做他?我不能接他的话锋,大是羞惭,心里怪母亲,为什么连这个也说。那时我已八九岁了。《从奴隶到将军》是在我们小学校旁边放的,名字就吸引人,更不必提它的故事了,其实在我小时,只要是打仗的电影,我都认为是好看的,我的伯父跟我意见完全一致,并且凡是我认为好看的,他也就认为好。而不少电影,也正是伯父带着我去看的,像上面提的这些,都是。
那时最不喜欢的电影,是著名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不用说,这是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,其片长达三个半小时,分为上下集,但我只看了上集,那时也只放了上集,是东村的人放的。电影里的镜头,记得起的很多,如张忠良演说时在黑板徒手画地图,忠良的老父被日本兵在树上吊死,白杨演的素芬给小孩补裤子屁股那儿的破洞,还有那个王丽珍给她干爹打电话,嗲声嗲气。上集的后面,是屋外下着大雨,素芬和她婆婆在床上,屋里到处在漏水。这是人间的悲苦,看了让人抑郁难过。二十年后,我在电视上又看了费穆导的《小城之春》,那也是解放前的老电影,拍于这部的后一年,也就是1948年。当时是从中间看的,一直就看到了结束,毫不枯燥。有人称《小城之春》为银幕抒情诗,大概不算过分,从艺术上说,它们有可一比,可以双峰并峙。但就是《小城之春》,我也不想再看,因为故事太单调,而气氛又太抑郁了。就像我后来看过的美国米高梅公司的《十二怒汉》,也无疑是一部杰作,其匠心独运之处,令人叹绝,但同样也是看过就不想再看了。有时候,你所喜欢的,不一定就是你认为最好的,而你认为是好的,却又不一定是你喜欢的,人就是这样的矛盾。看电影是如此,读书也是如此,就是穿衣、吃饭及行事,也莫不如此。
那时的电影,是由各村子出钱,请县里的放映人员来放,所有的电影,都是在露天看的,看电影的人,也只要晚上跑路(但对我来说,也有因为夜黑路远而不被允许去看、因而错过的电影,如《黑三角》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《神秘的大佛》《画皮》等),自带椅凳,不必花钱买票。也就是说,那时的所有电影,无不是免费的。小孩子个子小,必须站在凳子上,才能看得到,所以往往要扛长凳。放映的时候,也有挑着甘蔗来卖的,边看电影边吃甘蔗,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我家的家教严,从没有买过甘蔗吃。有小包装的葵花籽卖的,又是晚一些时候的事了,那应该是1983年后才有的,那时已建了电影院,很少再露天放电影,看露天电影的时代从此过去了。
从那以后,我看电影也就少了,我所记得的,在电影院看的电影,有《西安事变》,有《四渡赤水》,还有潘虹主演的《杜十娘》。无论如何,这些电影的味道,在我看来总不及在露天里看的好,看电影前的买票之拥挤、喧嚷、争执,看电影时的屋子之窘狭、气闷,都使人生出不适,减损了电影本身的快乐。而城市的坏处,在电影院看电影时,我也初见了端倪。
英国诗人库柏说过,城市是人类造的,而乡村,则是上帝的手笔。是的,一切的简朴之物,包括人和事,都是自然的初心。